中國佛教協會
編者按: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以“交流互鑑、中道圓融”為主題的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將於福建省莆田市舉辦。香港理工大學榮休校長、精進慈善基金會長潘宗光向本次論壇提交論文《淨土初祖慧遠:文化交流的啟示》。以下為論文內容:

前言:霍金的憂慮
霍金曾給人類忠告:不要主動接觸外星人!
其理由是:在西方歷史中,不同文化在交流時往往出現較優勝的一方侵略另一方的情況,假如和外星人交往而地球人類是被侵略一方的話就很不妙了!
他的擔心反映了西方人對外來文化的憂慮,那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由於過往歐洲人所採用的單邊主義,導致歷史上對各地如美洲、非洲、澳洲等土著文明侵略和滅絕。

這很大程度上經由宗教而促成,因為西方宗教主要是阿伯拉罕宗教, 即由舊約聖經發源的三大宗教: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信奉新約的教派)、回教、猶太教。
其所造成的思維強調唯一和絕對,便難免會孕育出強權和教條主義,較少運用同理心去考慮對方處境。由於歷史條件和宗教因素, 西方人常會將自己心理投射到現實境中而造成錯判。
與此相反,我卻認為應該保持樂觀開放的態度,因為歷史上還有其他的交流方式,例如佛教的傳播交流就是強調互鑑圓融。
歷史證明,單邊主義不可能達到這高水平的交流方式,因為無論怎樣大的帝國最終都會帶來分裂和自毀,陷入文明周期的終結。五千年的中國文明似乎能超越文明的周期性,而我相信有能力作溝通的外星人也應已摒棄單邊主義才能達到高階發展。
和西方不同,東方文化是以交流互鑑的形式來進行,我這樣來定義圓融:通過包容、理解來提升雙方文化水平的協同效應。以下以淨土宗初祖──慧遠來為大家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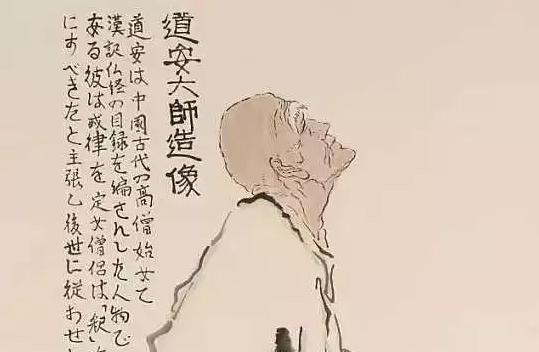
佛教從印度傳來中國,首先將這文化交流結晶的人可說是道安。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後,儒家以外的學問能站在中國土壤上爭鳴的就只剩下道家。然而,經過道安的努力,佛教確立了鼎足的地位,成為推動中國文化的三頭馬車。
例如,他為中國僧人定姓,凡佛教出家者皆改姓釋。此舉非但打破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之見,同時也實踐了佛陀四種姓平等的理念。
他亦曾為佛經訂立目錄《綜理眾經目錄》,成為目錄學的先驅,讓後人能對佛經進行系統性的考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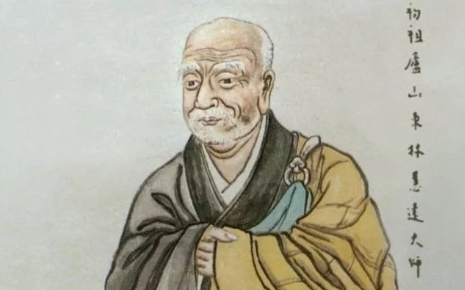
道安門下弟子眾多,其中最皎者是慧遠。當年道安派遣弟子們四出弘法,對他們囑咐有加,唯獨對慧遠不置一言,他跪下追問,道安便答:“如汝者,豈復相憂?”
據載,慧遠在二十四歲的時候便已升座說法,亦曾提出“本無義”理論以破斥道恆“心無義”之說…如此種種皆顯示他的慧解高超,難怪道安對他完全信任。
文化交流必須深入理解
早期佛經翻譯經常用上格義法,即將佛學名相和傳統文化的術語配對,用儒、道兩家的學理來闡釋佛理。
這無疑會讓國人較容易接受外來的佛學,可是同樣也會構成誤解。因為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的不同,概念的意涵也就不一樣,配對起來難免出現差錯。
例如,過往用“五行”去配對“四大”,四大是古代印度(和希臘)沿用的物理形態分類(地、水、火、風,分別像徵:固態、液態、能量、氣態);但五行所指的卻是自然界中相生相剋的過程,遠較物理形態的分類深刻得多;兩者差別猶如像牛頓力學和量子力學的兩種觀念,若等量齊觀便難免造成誤解。
故此,道安反對格義法,他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

但慧遠在解經時“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是惑者曉然”。即慧遠能模擬莊子來解釋佛經,消除信眾對佛理的疑惑,於是道安“特聽慧遠不廢俗書”任由他繼續用道家的觀念來闡釋佛理。
由於慧遠能掌握兩種不同宗教的理念,看出兩者相同之處並加以融匯貫通, 解說起來讓人更易明白。
然而,對一般人來說弄懂一門宗教已經太難了,能做到道安所講的“世典有功”,即使“未善佛理”也很了不起。故此,他只允許慧遠, 而不允許其他弟子以格義法來解經。
由於慧遠能夠掌握不同文化的理念,在學習來自異國的佛學時,也能尊重本國的儒、道思想;於是他能擺脫教條主義,即不必僵化地預設信仰的必然正確,而能夠以適合對方文化背景給出圓融的答案。
例如,桓玄質疑佛教(削髮為僧) 不合乎儒家孝道而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慧遠便即回答:“立身行道。”原來桓玄按《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來提問,而慧遠也按《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來回應。
這智慧的回答就體現著其本身對儒家的深刻理解,而不必靠硬銷佛學教條來說服對方,故此獲得當時文化界的尊崇。就像鳩摩羅什對慧遠的讚嘆:“邊國人未有經,使暗與理會,豈不妙哉?”

交流不應只看表面的名相術語,而必須要深刻掌握不同文化的理念;尤其要先掌握好自己文化的理念,這樣去理解外來文化才能有所成就,為知識作出貢獻。
學習外國文化也要先學好中國文化,道理很明顯:若連對自己的文化也不理解, 試問又如何能深刻理解外來文化呢?那就只能停留於表面化的堆砌模仿罷了!
另外,補充一點:用比較研究法來詮釋兩種學問的相同地方無疑是可取之法, 但也要留意兩者不同之處,這樣才能理解得全面和透徹。
例子可參考剛才所講的“五行”和“四大”的分別。能夠分別不同之處便可以對信息加以篩選,亦可減少穿鑿附會;這樣的訓練非但只令思維更縝密,亦有助於精簡今時今日的巨量信息。
全面的佛法事業:三無漏學
雖然慧遠的解經得到各方認同,但他的弘法工作並不停留於模擬詮釋的層面,他還致力尋找經律和促進翻譯,不斷探索佛法原意。
他派遣弟子法淨、法領遠赴印度求取經典;並在廬山般若台設立譯場,成為第一所中國私立翻譯學院;請來罽賓僧伽提婆重譯《阿毘曇心論》與《三法度論》;後來覺賢(佛陀跋陀羅)自北方來到廬山,慧遠也延請他譯《達摩多羅禪經》並為之作序:“夫三業之興, 以禪智為宗…”

由此可見,他所重視的不單是經文,更重視定學。而且他還重視戒律,請曇摩流支繼成《十誦律》的翻譯,使戒律得以在江南流傳。
由此可見,慧遠的修為不單在於對經文的高超慧解,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探索精神,使能全面掌握佛法核心主旨(三無漏學:戒、定、慧)。假若欠缺了戒學和定學,無論對經文的慧學有多高超最終只會流於玄談,失卻佛法修行的根本。
積極入世處理僧務
慧遠雖然隱歸於廬山,可對佛教事務卻極為關注,除了努力推動經律的蒐集和翻譯外,他還積極處理僧伽事務。
例如,覺賢在北方被排擠的事件,慧遠就明確評價和出力調停。
當時覺賢來到中國,掛單在秦主姚興之處,可能是由於持戒精嚴(“唯賢守靜不與眾同”《高僧傳》)的關係致遭鳩摩羅什的門人妒嫉,於是他們藉著一些未證實的傳言(“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同高僧傳)將覺賢排擠,令他遠走南方至廬山處。
慧遠歡喜相迎待之如舊友,並高調評價事件,明確指出錯誤一方在鳩摩羅什弟子(“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同傳),而非覺賢本人犯戒(“亦於律無犯”同傳),並著弟子曇邕寫信給國主姚興及關中的僧人以解除覺賢被擯之事。
可覺賢再也沒有回到北方,而是留在南方繼續翻譯工作,除了剛才所講的禪經外,還有僧祇律、觀佛三昧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十五部,貢獻可謂不少!
分析一下事件便可以看到慧遠對戒律道德的重視,對翻譯和奉行戒律不遺餘力,這不獨令他在處理僧務時能有明確的公正立場,亦令廬山僧人有較高道德水平。
故此,當桓玄要對僧人“沙汰”進行整頓時,唯獨廬山能倖免(“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同傳)。
反過來說,慧遠亦贊同將不合適的僧人淘汰, 因為他深感“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但他提出要保留合乎戒(興建福業) 、定(禪思入微)、慧(諷味遺典)標準的僧人,這些合情合理的標準亦為桓玄所接受。

時至今日,那依然是處理僧務的最佳典範,值得現代佛教借鑒:首先,要以戒律來確立佛教道德標準。
而且,有德之士亦要按律典積極介入僧務,這顯然能助提升佛教水平,才能在社會中備受尊重。
最後,當部份僧人道德下墮而遭社會遣斥之時,既要袒誠而不護短偏私,也要挺身而出維護正當修學的人。
事實上,僧團的道德既要能適應社會,亦要高於社會,才會獲得世人尊重。
例如,佛世時候因出家風氣盛行,釋家族許多年青人跟隨佛陀出家,於是淨飯王向佛陀請求,要未成年的人先經過父母批准才可出家;佛陀便為僧團訂立戒制, 禁止僧人為未經父母批准的未成年人授戒,這些就是為適應社會要求而製訂的戒律。
然而,佛教也有高於社會要求的戒律,如“四非事”則必須嚴格遵守才配作出家人,否則的話便會被驅逐出僧團。
佛世時僧團就是因為有明確的戒律支撐,因此廣泛得到世人尊崇令佛法大行其道;同樣,廬山能秉持高尚道風,才能得到尊崇,為佛教在中國爭取到一個穩固的立足點。
《沙門不敬王者論》的戒律精神
東方文化交流注重道德修養;而不像過往西方國家般將宗教和貿易、政治混雜。宗教道德和社會存在著互動的辯證關係,水平處於較低的一方自然會向對方表示尊敬。
當年道安在中國推動佛教,因為時局動蘯而面對很多社會壓力,而概嘆“不依國主、法事難辦。”
作為弟子的慧遠卻青出於藍,寫出了著名的《沙門不敬王者論》讓佛教在社會上站隱了腳步。

事緣桓玄在提出“沙汰賊住沙門”後, 再提出沙門應該禮敬王者的問題;慧遠回答了桓玄,後來再著論闡發他的理由: 作為出家人的沙門,捨棄世間風俗是為了成就高尚志向,因此衣著和禮節自然不和世俗相同,這才顯得出家隱居的高尚風格;而這樣的做法也不會違背世間孝、敬的道德本義。
反過來說:若穿著並非宗朝之服的袈裟、手捧著非正統祭祀的缽盂、已捨棄本國形象的削髮僧人,以異國容貌來行中國禮儀,難免出現不倫不類的場面。這樣的辯解倒是把桓玄折服了!
慧遠可說是捍衛了佛教的根本價值,因為若要僧人按俗例禮敬王者的話,就會分心於俗禮而無法專注於修行,無從解脫。
事實上,印度傳統對出家修行人極之尊重,非但沙門不敬王者,而是反過來王者禮敬沙門。
例如,前述的律藏大犍度所載,作為父親的淨飯王在見面和離開的時候便禮敬佛陀;又如,在長部沙門果經中,阿阇世王前往佛陀處參學時也是禮敬佛陀的。(桓玄當然不會簡單接受外國風俗,他詰難王謐:“外國之君,非所宜喻”弘明集卷十二)
但無論如何,慧遠確實掌握到作為異國文化的佛教特質,並且毫不退讓,堅持將之注入中國佛教中。
注重實修創立蓮社
道安可說是開拓淨土思想第一人,他曾齊集七人在彌勒佛像前一起發願往生兜率天宮。
三十年後(402)弟子慧遠又再青出於藍,帶領一百廿三人在廬山的阿彌陀佛像前,集體發願前往西方淨土,並創立白蓮社作為開宗立派的標誌,後來淨土宗、禪宗、密宗成為中國的三個最大宗派。
蓮社的創立,本質上就是體現著自度度他的菩薩道精神,既發誓向阿彌陀佛表白自己心跡;亦團結互助,以互相提升修行境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策徵之道”《高僧傳》)。
由於念佛法門簡易實修,並不需要玄奧的義理,更易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慧遠的念佛修行源於《般舟三昧經》,達至定中見佛,他亦嘗和鳩摩羅什討論(《大乘大義章》第十一問)。
當時佛教界對鳩摩羅什所傳的禪法頗有微言, 認為他“沒有師承、不講源流、不得宗旨”,慧遠指出“雖其道融,蓋是為山於一簣”,而他推崇覺賢的禪法即在於其能貫通大小乘。
荷蘭佛史學者許理和(E.Zurcher)曾指出:慧遠對於阿彌陀信仰和修行技巧通俗化之外,對於禪法更感興趣;他畢生致力於禪法和戒律的追求;為禪經的匱乏而抱怨,為譯本的出現而喜悅;更有可能為實修而放棄毗曇學的研究。
由於禪修不是今次論文的範圍,我也就不深入討論了,但只需要留意慧遠注重實修的態度,以及他劃時代的貢獻—— 把究竟和方便兩者圓融一體,那就很有啟發性了。
從實修而言,我更注重淨土宗的三個特質:一,崇尚他力;二,末法時期的方便法門;三,自度之餘亦要度他。
若從這三個角度去理解的話,便能明白念佛法門的普及價值,或能有助於推廣佛教。所謂末法時期,也不必區限於時間上的分類,而可以從地方性來理解, 即鳩摩羅什所說的“邊國”,就是指遠離印度的地方缺乏佛教經律而導致修學障礙。
若從這角度來看的話,慧遠所處的文化背景也可算是末法時期了。因此,念佛可說是超越時空的方便法門,對於修學佛法有困難的朋友不妨一試。
結論與啟示

慧遠的貢獻
先簡略總結慧遠的貢獻:雖然是高僧道安弟子,卻能青出於藍;雖然國學造詣極深,卻能抱包容開放的態度學習外來文化;雖然慧學極高超,卻仍不斷探索追尋佛教經律的本源;雖然隱居廬山不拜權貴,卻仍積極入世處理僧務;雖然未有完整的律學,卻身體力行來堅持戒律精神;雖然未有完整的定學,卻仍注重實修創辦白蓮社。
既要學習也要批判
慧遠的學風和人格充份反映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我們在學習之餘,亦可藉鑑為現代交流的啟示。
現在,我們身處東西文化接觸的交匯點,既要虛心學習西方文化,也要學會批判,這樣才能作出更深層次的綜合。
例如,我有興趣涉獵霍金的宇宙學,嘗試理解他的學說,但也會批判他對外星人交流的觀點,因為那顯然是局限於西方歷史,而沒有考慮到東方的交流方式。
而且,我認為他所講的開發外星資源並非人類當務之急,我更強調先開發心靈資源以充實人生,因為快樂和幸福是源於內心而非外物!
我認為無論科技有多發達、外太空去得多遠, 若欠缺認識心靈的智慧,內心仍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快樂,人民內心的紛爭在西方國家轉化為內部分化、槍擊不斷,而對國外則實施強權政治、單邊主義。

相對性的關係
中國文化以佛、道、儒為代表,沒有單邊主義的絕對化思維,強調的是相對性的關係,三者均體現著平等、慈悲的精神。
這種相對性關係也充份反映在醫學之上,中醫是按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原則來理解生命,各個器官的功能既互相協調交疊也互相制約。
西方醫學通過解剖個別器官來湊合出對生命的理解,也就要先把器官和生命切割開來。量子力學家波爾對以切割方式來理解生命曾提出異議,兩種醫學體系顯然分屬兩種不同的理解範式(paradigm),這裡不深入討論了。
但指出儒家專注於人和人的關係,所解決的是社會問題;道家側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趨近自然的人生觀有助於解決環保問題;佛家強調人和自己的關係,直接面向心靈問題。
我認為這三個層次體現著全人類的一切開系;假如處理得宜, 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假如處理不好,就只能治標不治本。
反過來看,西方宗教強調人神關係,導致現實人生的問題被架空,非但沒有徹底解決問題,甚至隱藏得更深,影響也更廣。
例如,歷史上的強權主義,導致現今的國際問題;又如, 資本主義的過度消費,導致現今的環保問題。
這些問題的成因和解決方法,無論直接或間接都和人們的意識型態、宗教取態有關。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在現代社會實在具有深遠的價值和意義。

面對逆境的應用
回看慧遠,他的國學造諧極高,讓他能善巧地處理多元文化的問題;以人為鑑,我們也應學好國學,因為無論儒、釋、道均有深厚的文化基礎以培育心智,均有助於人們在現代社會面對逆境。
例如儒家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這都鼓勵人們培堅養忍態度以超越一時的逆境。
至於道家老子所說“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以互相依存的相對性角度來看人生禍福悲喜, 那很接近佛教空理所指出事物無常、無我的相互依存性。
若現代人能熟習佛、道儒的哲理,即能以傳統智慧來看待人生的話,必然有助提升面對逆境的能力。
順帶一提,我接觸過一些從偏遠山區初來到國內大學的年青人,他們向我訴說:在大學裡經常和人比較而自感不安。不難理解,那是他們心中自卑感作祟而經常和他人的亮點作出比較。
雖然佛教並不贊成比較,因為比較會產生分別心, 但對於未經佛法熏陶的年青人來說“比較”心態在所難免。
我鼓勵他們要比的話就向上比,見賢思齊以激發上進心。同樣也要向下比以增長慈悲心,這才會更全面。
因此也要反思:從山區中能考進大學實屬難能可貴,故必須珍惜機緣創建成就以回饋社會。即使是條件所限而輸在起跑線,但只要堅持不懈,我相信努力的年青人最後還是會贏在人生的終點線。
努力吧,總不會白費的,這正正是佛教成語的意思:功不唐捐!
然而,除了調節心境,佛教亦有解決問題的具體技巧如四聖諦,簡單來說: 遇到煩惱就要先確定問題所在(苦)、並且審查成因(集)、接著訂立解決目標(滅) 、然後製訂方案並貫徹執行(道)。
雖然以上都是一些題外話,但我想強調的是: 佛學作為文化交流便應和社會接軌、和現實相應,才會為大眾所接受,那正是淨土祖師所給出的啟示。

具體的發展形式
要確立文化定位,具體的形式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慧遠要在中國推動佛教, 使之和儒、道並駕齊驅,他努力將定學和淨土思想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具體的修習形式,讓信眾能從之而契入佛理,這樣淨土宗逐漸把意識凝聚起來成為佛教傳統。
同樣,在現代推動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也必須有具體形式才能促進大家的意識,而這些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活潑的。
例如,我曾在全國政協推動將中國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訂為例假,現更希望將來恢復有中國式的父親節和情人節。
當然我並不希望像西方節日那樣淪為消費娛樂的日子,而是讓民眾藉此反思其中的歷史意義。這樣通過具體的形式有助於加強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和理解。
從具體的實踐出發,我們可發揚中國文化的理論,讓更多人得益。
例如,在學校課程中可以納入更多的古代文言範文,好讓學生們更多接觸;又如在政府機構將之加進入職試範圍,好讓知識分子們有更多理解,也更人性化地為國民服務。
現在,最理想的就是能集合各教的研究力量,綜合出一個具體而全面的教理和規範,讓民眾可以在不同角度來契入中國文化。最終成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圓融文化高度的體現
在交流的過程中也顯示了中國文化本身極富於包容性,故和外來文化交流時並非單向的汲收,而是經互鑑後再圓融地創生出新理念,例如漢傳佛教衍生出淨土、禪、華嚴、天台等等各宗派。
反過來看,若其中一方未能達到相當的文化高度,便難以出現多元文化的協同效應,也無法產生出創造性思維以超越原有觀念。
即如淨土宗和禪宗傳到日本而大盛,表面上看,禪宗是被日本禪者(如鈴木大拙等)推上了世界舞台;可仔細分析起來,日本方面除了在儀式上更為系統化之外, 似乎並沒有超越其中的宗教哲理,兩宗本質上仍是富於中國特色的宗教。
故此,在學佛修行的同時,我相信學習中國文化有助提升圓融的能力,可為人類創造更崇高的文化價值和精神素養。
當然,隨著社會進步,我們就必須對傳統作更深刻的發掘、和現代社會作更高度的綜合,以避免重蹈清代八股文僵化思維的歷史覆轍。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中道圓融的方式不獨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個別例子,也是歷來整個佛教的交流方式,包括南傳斯里蘭卡、泰國、緬甸等地;北傳中國,再傳至外圍地區如韓國、日本等;推而廣之,也包括儒、道兩教的對外交流。
這一切皆是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因為東方文化的優勢體現並不在於強權武力,而在於道德和智慧。
目前社會世風日下,往往忽略了道德誠信對人格和事業發展的重要性,在表面成功背後埋下了煩惱的伏線。
作為佛教徒更應注意戒律的確立和奉持,僧團應以身作則成為世人道德模楷,摯誠的道德實踐便是智慧的開始,也為人類和社會增添光輝。



